
我的故事情節當中,沒有遇見像「越離非洲」(Out of Africa)中,那樣堅強的梅麗史翠普(Merry Streep),也沒有機會當羅勃烈福(Robert Redford)舉槍瞄準草原上的野生禽獸。我身上最寶貴的是那臺黑色相機、多卷菲林,還有一疊傍身的美金。我的所有資產僅此而已。
我透過自己手中的鏡頭,直視他們。然而,那樣的神情和可怖的決意,使我不經意恐懼。焦距在顫抖。是什么讓他們的眼神之中,挖去了靈魂,遺留空蕩蕩的,無盡漆黑墨色的──恨意、憤怒、死亡──把一切出賣給撒旦,換回的──
我已經分不清誰是圖西族人誰是胡圖族人,我姑且稱他們為黑色人種。
今天有人警告我,城里的黑人們都瘋狂了。我們這些外人也同樣處境堪危。傍晚,趁日落余光,我從位于三層樓高的住處窗口望出去,盧旺達的基加利靜謐得教人發顫。深夜夢里依稀聽得房外走道滴滴答答,盡極所能腳不落地。
白天扭開收音機,那把惡毒的男人聲嗓,繼續深沉、齷齪、狡猾的慫恿哄騙逐漸喪失意志的胡圖:“殺光那些該死的圖西蟑螂,他們不配這片屬于胡圖的土地,殺──光──他們──”
聯合國極盡所能,把所有白人都遣走,把極少的驚慌中殘存的黑人帶走。我和少數人留下,記錄一次次的迷失和死亡。在我醒着的時光,手不能停,“喀達、喀達”快門幾乎被拇指指紋給磨平了。
直到一切攀過末了,我終于可以停下來喘息,從事件蔓延以來,現在才有機會做的一件事──是為盧旺達哀泣。
那都是一九九四年的往事了。
文/宣春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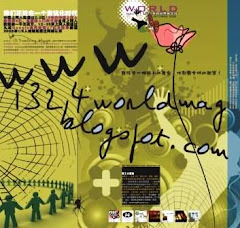

没有评论:
发表评论